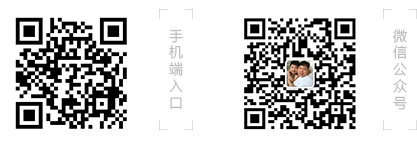时间: 2024-01-30 22:00:31 | 作者: 废旧拉链分离设备
如今市面上有许许多多关于女性主义的书,呼唤大家从混沌中觉醒、重新认知自己,打破层层束缚、找到独立自由的本我。可在生活中,一个女性的觉醒往往是用漫长的一生去完成的,是由无数个看似“失败”的选择、决定一点点累积、形塑出来的。在郑在欢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中,我们正真看到了大雪、春蓝、秋荣三位个性迥异的女孩让人唏嘘的生命故事,春蓝似乎是其中最普通、最没有戏剧性的一个,但看似平平无奇的命运背后,是一个女孩在成长过程中被遮蔽和忽视的痛苦——在生活的日常中被牺牲,被剥夺。
春蓝是一个爱家人、团结家人的人。她愿意理解家人,她总以为再牺牲一点、再忍一忍就会变好,但后来发现无休止的付出是没有尽头的。在接纳父母的爱的过程中,她始终是被压抑着的。她说不清自己受了什么样的“压迫”、做出了什么样的牺牲;更不知道该怎么怨自己的父母、什么限度的付出才是合理的。直到后面她慢慢识别出了父母爱的诡计,但并不知道如何反驳、申诉,她甚至不能说父母的爱是假的。她能做的,只有逃离。
春蓝觉醒的过程,是她用三十年的生命写就一个长篇故事。她选择过被动的接受,也选择过主动的逃离。小说临近结尾,似乎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答案,怎样才是更好的生活,正如我们每个人对于什么是正确的人生一无所知一样。今天单读摘录了《雪春秋》一书中,春蓝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一些碎片,她的生活始终在家乡与异乡、困境与自由之间打转,她一直在寻找答案……让我们大家一起走近春蓝,走近一个女性漫长而深刻的觉醒之路。

春蓝站在西地的河岸上,带着笑模样。快到夏天了,麦子越长越高,野花拼命地开,蝴蝶和蜜蜂也都兴高采烈地飞。她脑中还印着父亲的笑,他笑了,肯定是好事,母亲一定生产顺利,毕竟都是第四个了。都怪刚刚走得太急,忘了问是弟弟还是妹妹。可别是妹妹了,是妹妹,抓住了还得罚钱。父亲笑了,肯定是好事,肯定不是妹妹。她很满意这个想法,不是妹妹,肯定不是妹妹。她哼哼两声。她认定了,不是妹妹。转过身,看到起伏的麦浪,晚春的风呼呼地吹,脑袋上的短发支棱起来,和麦芒一样锐利。她刚卖过头发。她早就想卖了,母亲一长长就卖,姐姐也是。姐姐卖了头发,母亲会煮鸡蛋给大家吃。她一直吵着要卖,母亲告诉她小孩子的头发不值钱,到了十岁才能卖。过了年,她十岁了,却没有卖掉。她的头发又软又黄,也不长,收头发的人不要。她躲起来哭了,等眼不红了,才回家。上个月,又来了一个收头发的,那个女人很好说话,要了她的头发,虽然给的钱不多。她高兴坏了,支棱着贴着头皮的短发,到处去找人玩,对大家说她卖头发了。王雨婷笑她的头发铰得太厉害,不好看,“跟狗啃的一样”。她不服气,和她吵起来。你的头发怎么卖不掉,她说,你就是眼气。她和王雨婷是最好的朋友,但是那天,她们两个都生气了。晚上,母亲煮了鸡蛋,大家每人只有一个,她两个。这顿饭可是春蓝请咱们吃的。母亲说。春红和春芳笑嘻嘻地看着她,春芳还来抱她,她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她只吃了一个鸡蛋,把另一个盖到碗底下,打算留着明天早上就稀饭。第二天,她掀开碗,鸡蛋不见了。母亲告诉她春红着急上学,拿着路上吃了。她鼻子一酸,险些哭出来,看到母亲的大肚子,她还是没哭。
在心里,她是想去的,对外面的世界,她也好奇,同时还能减轻家里的负担,这是两全其美的事。可一想到要离开学校,她就忍不住心慌,成为尖子生之后,她没有掉出过前五名,老师们对她青睐有加,断言她考上大学不是什么难事。村子里没出过几个大学生,回来基本都做了老师,她也想做老师,像曾经的语文老师那样,用短短几句赞扬鼓起一个孩子的雄心,似乎没有比那更好的事了。她一直做着这样的梦,直到上学路上的同伴渐渐消隐,到了初三,已无几个女生可以同路了。这样的变化让她心慌,她还在上学,她知道这是不合常理的,人家都开始挣钱了,她还在花钱,而母亲,总在念叨缺钱。中学需要住校,她很少再有时间帮母亲洗衣做饭,每次回来她都抢着干活,可母亲似乎已经不习惯她的帮助了。
“妈,我不上学了。”她反复想着这句话,反复走在无人的河岸上。岸上布满脚印,天似乎又要落雪,潮湿的暮色像一床破棉被从天边铺开来。鞋子湿了,那是母亲做的棉鞋,不适合踩雪。她顶着西北风往家走,脑中循环播放着那句还没说出口的话。晚饭过后,她来到厨房,母亲正在归拢剩饭,你说说你们,现在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,那么多肉都剩下了。母亲捡出一根鸡腿,递给她,赶紧把这个啃了,你看你瘦的。她接在手里,没有吃。生活,看来是真的变好了,以往为了一个鸡蛋都能拌嘴,现在鸡腿却剩下了。如果出去打工,会变得更好吧。她叫了一声妈,鼻子却酸了。她赶紧低下头,那样子像在吃鸡腿。母亲收拾完了,在她身边坐下,摸了摸她的头说,咋还不吃,等会儿该凉了。她抬起头,看着母亲,不知道该说还是该吃。母亲率先开了口,昨天赶集回来,我问了王雨婷她妈,她说那个活儿不累,还能学技术,踩缝纫机,学会了就是一辈子的手艺......母亲见她没反应,又说,我也不想让你出外,谁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呢,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,人家都在慌钱,咱们不慌能行吗。过了年,我也上北京去,把你小弟送到城里上学,让春芳跟你奶奶。你小弟上学得花钱,还得给你奶奶钱,钱——你别说了,我愿意。她打断母亲走出门去。来到院子里,她仰起头,不让眼泪流出来。雪,又洋洋洒洒落下来。过年,本是喜庆的日子,可过年,却总是下雪。

原来收音机才是生活必需品,比牙膏和肥皂作用还大。干活儿的时候,所有人耳朵里都塞着耳机,除了哑巴,他什么都听不见,所以干得最快。电动缝纫机的声音此起彼伏,不间断地冲击耳膜,十三个小时之后在床上躺下,耳朵里还回荡着长长短短的机器声。声音的长短取决于哑巴干活的速度,他是这里最老的工人,已经二十五岁。一个房间那么多机器,只有他脚下那台能发出那么频繁且均匀的声音。哑巴长得挺好看,但没给她留下好印象,因为他总是嘲笑别人的工作,新人难免会犯一些低级错误,本来就羞,他一笑,更加无地自容了。还有他看人的眼神,总是色眯眯的,这让春蓝觉得恶心,所以总呛他。哑巴听不到,她说什么,他都笑嘻嘻的,这让她更生气,兴许他还认为自身看上他了呢,想到这里她简直气不打一处来。那么讨厌的一个人,却将他制造的声音深深摄入她的脑海,如影随形,逃无可逃。工作时每个人都跟哑巴差不多,反正也不许聊天,还不如哑巴呢,他有天然的屏障,不必用耳机阻挡噪音。老员工每人驾驶一台机器,看起来高高在上,新来的只能干一些杂活,听任老员工差遣,搬一张小马扎辗转于机器之间,剪线头,穿拉链,修剪缝合处,用火烧去包边带上的接头,再用手按牢......所有工作都要低着头,眼前是踏板上扬起又踩在的脚,轰鸣的电机刚好悬在头顶。噪音最终会沦为背景音,脑子被一种奇怪的寂静占据,大概是长时间不说话的缘故,有人,却不能说话,以至于常常猛然发觉在脑中和自己说话——也有一定的可能是和别人,说了很久才发现并没有说出口。总是恍惚,像是身处旷野,辨不清方位,像被关在密室,找不到出口,像做梦,没有醒来的方法。
有一户特别合适,这话说得有点奇怪,她只是一个人,与之匹配的却是一户。她当即拒绝,说不见,接着又说,我还小。本地人说话,遇到好事至少要拒绝两遍,第一遍多被理解为谦虚,第二遍才开始当真。具体到家人之间,情况又不一样,很多事情,即使拒绝成千上万遍,还是会被理解为是为家人着想而不是出自本心,家人则只能反过来以为你着想而一意孤行。好像个个都是赵匡胤,必须要为其披上黄袍才能作罢。你不用舍不得我们,母亲说,你要是过好了我们也就好了。她换了几个角度拒绝,母亲仍旧用这句话应对。她知道再多说也是废话,在心里,她打定主意,就算对方是天兵天将也绝不松口。

她以为会轻松不少,确实也轻松不少,不过远没有想象的轻松。何时下班,取决于最后一桌客人何时走,还要祈祷这期间不要再有人来。磨蹭到最后的往往是喝酒的人,桌上的菜不剩什么了,含混不清的醉话慢慢的变多。她脾气太坏,算不上一个合格的服务员,对这些点不了几个菜还总赖着不走的醉鬼向来没有好脸色。醉鬼们也不在乎服务态度这码事,将她的揶揄嫌恶当作调情,趁着酒劲儿跟她斗嘴,让她火更大。妮儿,再来一瓶。没有,菜都没了还喝个屁。那再来个花生米。花生米值几个钱,心疼钱喝什么酒啊。你这妮儿,年纪轻轻怎么那么现实,张口钱闭口钱的。不为钱谁在这儿伺候你们呐。好好好,再炒个尖椒肉丝,行了吧......要是她愿意,可以把这种对话一直进行下去。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火气,对这帮过穷瘾的男人一百个看不顺眼。她苦着一张脸坐在旁边的空桌上等他们走,仰头看着电视,偶尔一两句酒话挤进耳朵,总能立刻分辨出哪些是大话哪些是真心话。她一点都不想关心,可听到了就没办法装听不到。大话听得多了也像真心话,肯定是心心念念的事,才会喝醉了酒还惦记着。无非是赚钱养家和挣钱成家这两件事,这话从男人嘴里说出来,最终往往指向女人。
我要回去结婚了,她说,所以不能和你们一起开店了。秋荣当即炸了毛,语无伦次地反对,好像要回家结婚的那个人是她。就算不开这个店,也不能让你这么作践自己。秋荣说,不就是欠那个男的钱吗,我帮你还。别啊,大雪也急了,要不这样,你那份我先帮你垫上,这样你就不用回去了。春蓝哭了,哭着哭着又笑了。大雪和秋荣搞不清状况,过来拍她的后背,揉搓她的手,如同抚慰一个抽风的病人。她抱住这两个萍水相逢的姐妹,彻底笑了起来,你们想哪儿去了,结婚是我自愿的,我那个未婚夫可有本事了,你们应该祝贺我。她努力让自己笑得灿烂,虽然脸上还挂着眼泪。秋荣忧心忡忡地看着她,一副完全不信的样子。她抹干眼泪,也不笑了,认真地说,等结了婚,我才有闲心回来跟你们开店,跟结婚比起来,开店可算不上什么大事。秋荣还是将信将疑,不过也没有继续反对,好吧,我们等你回来。坐在回家的车上,她的心是慌的,不过很快就急切起来,像一个真正的新娘子那样,虽然她的新郎——那个腰上总挂着一串钥匙的稳重青年——她没见过几次。赶紧结吧,快点结吧,她想,结了婚,一切就能了结了。

女儿断奶后,她重提去杭州的事。婆婆和丈夫依旧反对,咱自家的生意都忙不过来,出去做什么生意。他们在打什么算盘,她一清二楚。刚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放她走,因为她没有完成生孩子的使命,她全力配合,乖乖受孕,以为了结了这事就没人管她了。闺女生下来,虽然谁都没说什么,但她知道,使命还在,甚至更急迫了。这时才去想,要是像母亲一样一连生三个都是女孩怎么办,要是像王雨婷她妈一样一直生女孩该怎么去办。来到婆家,她没有唱过一句反调,看不顺眼的事情还是很多,但她学会了不说。总感觉自己是个外人,没有同盟,孤军作战。
背着所有人,她偷偷去打避孕针,一个月一次。这是没有很好的方法的办法,还是因为想到这个办法而兴奋莫名,当然,凄惶还在,或许正是因为太过凄惶才生出兴奋,又因为兴奋过了头才觉出凄惶,加水,加面,还是笨媳妇那一套。有一次,丈夫在身上徒劳奋战的时候,她笑出了声。咋了。他瓮声瓮气地问。没咋。她说,就是觉得你好逗啊。这话无异于讽刺,丈夫平时少言寡语,跟幽默一点关系没有。他干什么都目的明确,工作卖力,因为能挣钱,在她身上卖力,因为能生小孩。他要是清楚自己生不出小孩会怎么样,就像他经营的这座废品收购站,全是报废的垃圾,丧失了原有的用途。她清楚自己多没有情调,再加上发胖变丑,要不是为了生孩子,他才不会吭哧吭哧往身上爬呢。打了几个月的针,体重一发不可收拾,她不敢上秤,不敢照镜子,无奈垃圾收购站里最不缺的就是这两样,各种能映出人影的垃圾,称各种垃圾的秤。她偷偷网购减肥药,吃得上吐下泻,月事也不规律了,有时来得晚,有时来得多,惶惶不可终日,怕避孕针无效,怕失血过多而死。为了不被人发现,每次都跑到那堆塑料山和真山交界的深沟里,吐,或者拉,流泪,或者流血,她连自己的身体也管不住了。有一天,她昏死在自己的呕吐物上,他们找到她时已是深夜。她在丈夫的摇晃中醒过来,清楚自己真的成了一个笑话。我想回家,她说,让我回家。
一天,一个远亲从门前经过,跟母亲聊起天来,我的老天爷,这就是你们家啊,真好看,真气派,这得花多少钱啊。气派啥呀,好看啥呀,母亲说,你是光看到气派,没看到花钱,连买带装修你知道花了多少不。多少?女人伸长了脖子等待答案。谈到钱,人们还是那么神秘。母亲伸了四个手指,女人发出惊呼,四十万啊!我的老天爷。还多呢,母亲咬着牙说。谈到钱,人们还是充满恨意。她和女儿坐在门廊里,没有参与这场对话,听着她们在门外兴冲冲地大呼小叫,她突然伤心起来,伤心到了疼痛的地步。她捂住胸口,痛苦地闭上眼睛。等那个女人走掉,她来到门外,对笑容还没散尽的母亲说,妈,我想离婚。
明白了她并非是说说而已,母亲对她发动了一场车轮大战,所有能说会道和自告奋勇的亲友依次登门,试图让她知道她错了。
你再想想吧。父亲说。姐,我支持你。春芳通过电话偷偷说。不管谁来说,她都不与之辩论,她清楚自己辩不赢。或许沉默才是最好的辩词。母亲很快看出了她的坚决,把很多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口才的七大姑八大姨拦在门外,转而向她抛出了一个颇具重量的条件,蓝,你不是一直想去杭州开店吗,你结婚时田玉家给的八万块钱让妈花了,妈再去借来给你,你去杭州开店,好不好。
她看看母亲,没再多说。丈夫和婆婆怒气冲冲地赶回来,要她给一个解释。她给不出来。丈夫在盛怒之下要带走女儿。她再次坚定起来,坚持要女儿跟她。好在只是一个女孩,婆家很快就不坚持了。母亲答应还的那八万块,当作补偿给了婆家。二十九岁这一年,她什么都没有了,得罪了所有娘家人,从婆家净身出户,只有一个两岁的女儿留在身边。她给秋荣打电话,要去她那里打工。打什么工?秋荣几乎喊破听筒,什么叫打工?我